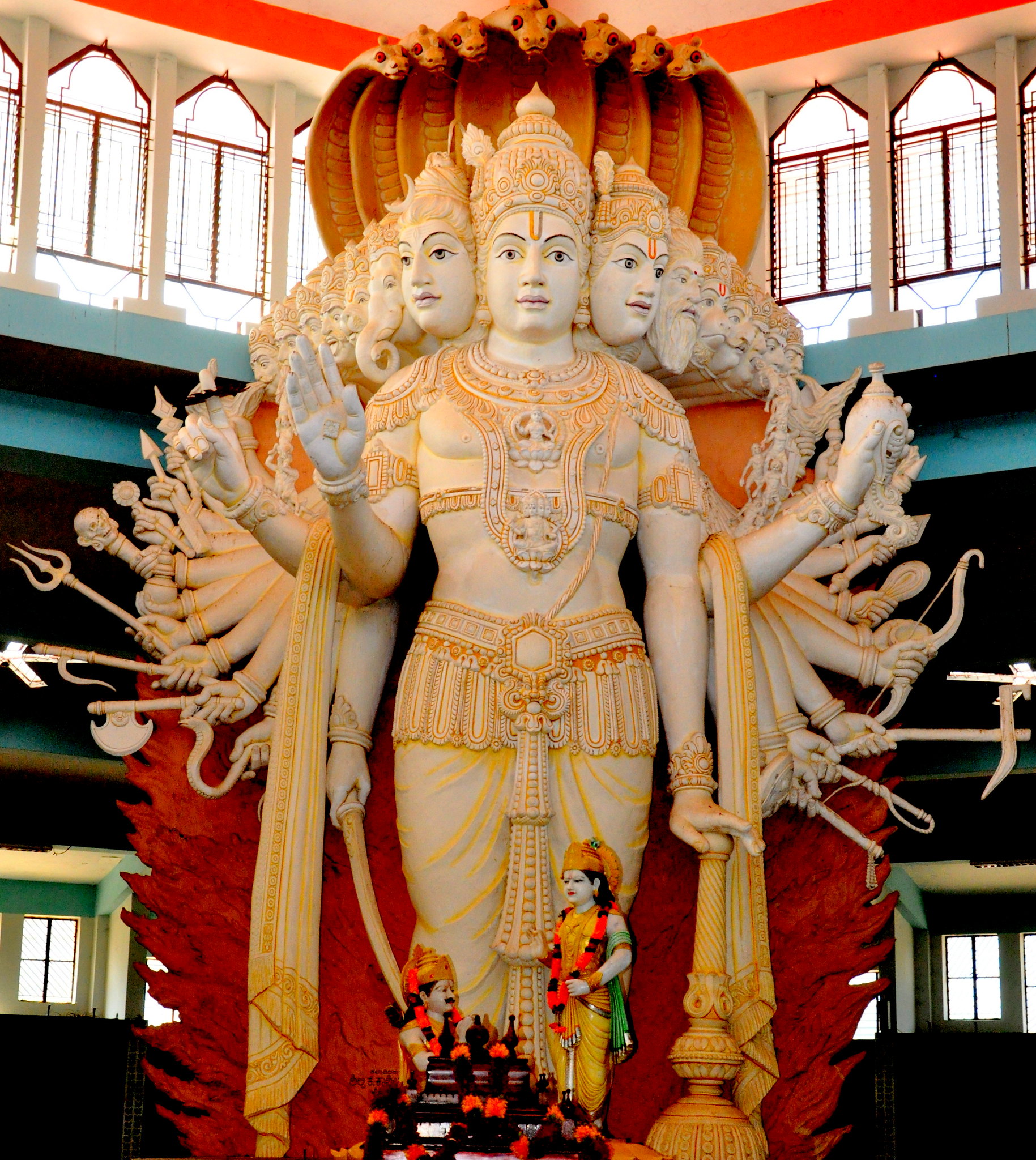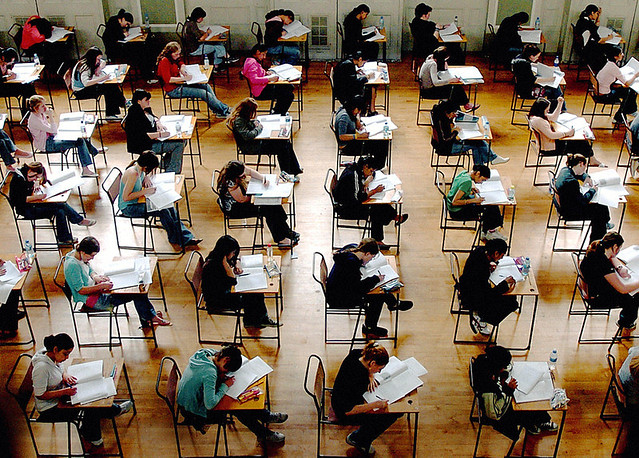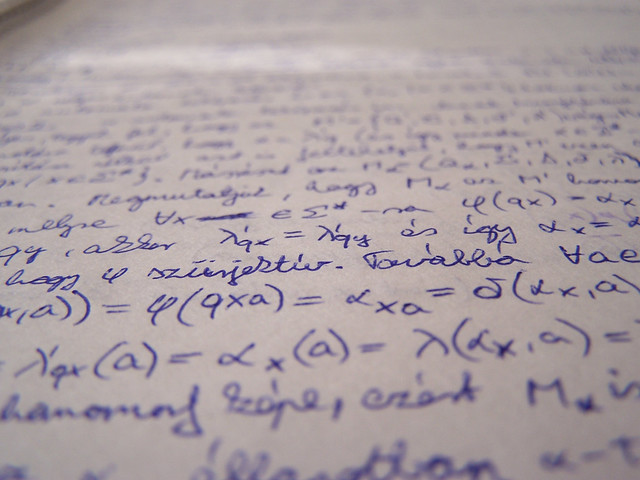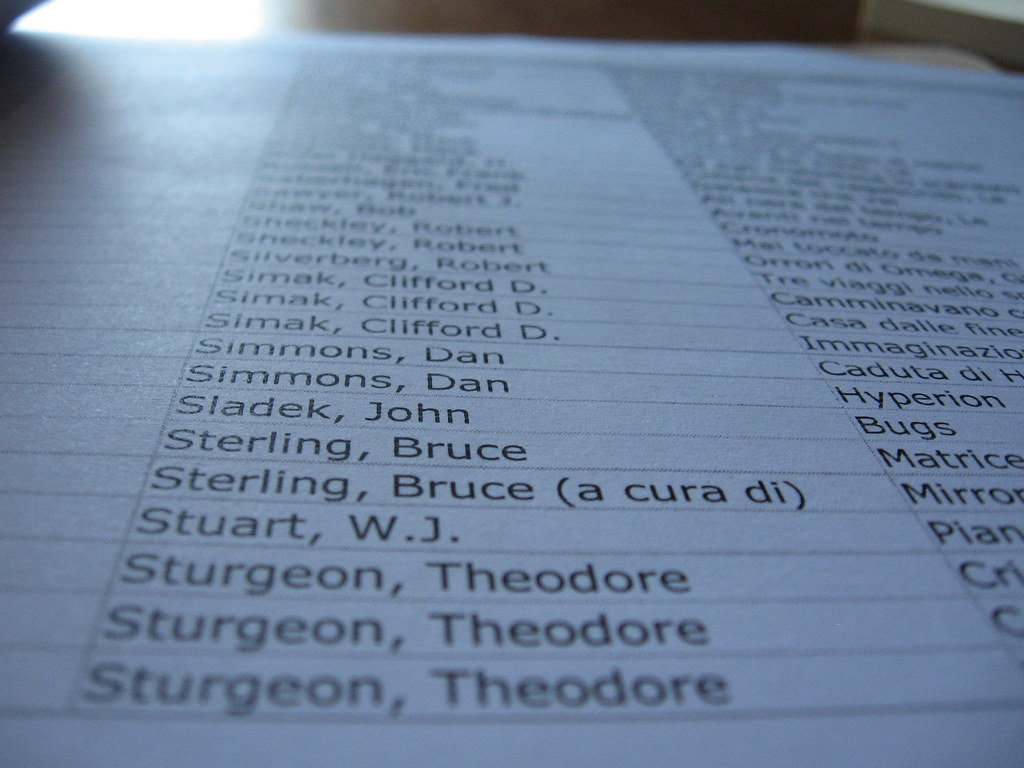從實驗的結果上來看,有三組實驗在這個問題上,有相當不同的發現。
除了依照事物的外表形成概念外,我們還有其它形成概念的方法嗎?
嬰兒和成人在外表上其實具有很大的差異,毛毛蟲和蝴蝶也是如此,但這不妨礙我們將這些東西歸成一類,形成概念。雖然形態改變,但是仍維持在同一個向度中,這個是事物的「本質」(essence)。人們因為直覺(naive intuition)而形成特定類別,叫作心理本質論(naive essentialism或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這並不是說它完全知道本質為何。例如知道「水」這個概念,並不需要知道它是組成分子為何,只要相信它存在某些特質即可。相信某個概念存在某個特質就是科學探索的起始。
對於比較抽象的概念,我們怎麼掌握?
有一些概念是比較抽象的,例如:「基金經理人」、「斷奶」、「CLIL」等等,在這些概念下的事物,應該存在某些基本特質使它們可以被歸類為同一個概念。既然如此,那關於這些抽象概念中,使事物間彼此有關的特質是什麼?我們對這些事物的知識又是從何而來的?
語詞和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角色:我們是否需要語言才能認識這個世界?
當詞彙進到各個領域的時候,詞語就會攜帶更多資訊量(Murphy & Lassaline, 1997) 。可以用紅酒課程來理解這段話。如果是一個紅酒新手的話,不論喝哪一瓶紅酒,大概都會有差不多的感覺,所有的紅酒都是「wine」。如果在紅酒課程中,反覆地聽到「這是Beaujolas,那是Merlot。」「那個甜甜的,這個比較澀!」這時候,我們會開始用「口感」去將感受到的紅酒進行分類,於是我們慢慢感受到紅酒之間也存在差別。(對此,Solomon (1997) 有不同的看法)
是詞語形成的類別讓我們去分類世界?還是事物本身的外表幫助我們分類世界?
Gelman and Markman (1986); Gelman and Markman (1987) 發現相同類別的感知可以蓋過相同外表的感知。例如告訴小孩子雷龍有一種特質(冷血),而犀牛有另一種特質(溫血),接著問小孩子三角龍有什麼特質?由於雷龍和三角龍被歸類於同一個類別,都是恐龍,因此小孩子傾向認為三角龍也是冷血動物,儘管三角龍的外形和犀牛是更接近的。
先有概念?還是先有詞語?
許多發展心理學家認為由於接觸到詞彙,就會使人們在陌生的概念間建立界線(例如:Bowerman and others (1996)、Gentner and Boroditsky (2001) 、Gopnik and Meltzoff (1987); Gopnik,Meltzoff and Bryant (1997) 、Waxman and Markow (1995) 、Waxman and Thompson (1998) )。
參加「2017年海外華語教師師資培訓營」有感:一個脫離當地脈絡的華語教學
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和正大管理學院舉辦的「2017年海外華語教師師資培訓營」主要有三種對象:第一種對象是成大華語中心招募、培訓的華語教師;第二種對象則是由教育部選送的華語教學助理;第三種對象是泰國在地的華語老師。前兩種對象都是中華民國國籍,第一種對象主要是有經驗的華語老師,通常來自各大學的華語中心;第二種對象則是台灣各大學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的學生。第三種對象簡單地說雖然是泰國在地的華語老師,但是背景是相對分歧且多元的。我沒有辦法認識所有在地的華語老師,但光我所接觸的老師就包括:實驗中學(以及國際學校)、一般大學、社區大學、中華會館的華語老師。培訓營的目標對象是第一種對象,後面兩種對象能夠參加培訓營主要是沾第一種對象的光。
參加「2017年海外華語教師師資培訓營」有感:華語教學離外語教學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台灣,台南市首倡以英語做為第二官方語言,市政府的第二官方語言專案辦公室和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在11月中進行「2017國小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同一年的,10月31日和11月1日、2日,我也參加了由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和正大管理學院舉辦的「2017年海外華語教師師資培訓營」。成大外文系和成大華語中心,雖然都來自台南,但是對於外語學習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
人們是先有思想才有語言?還是先有語言才有思想?自已給個心理的演講。
「心理的演講」(inner speech)也被一些人視為是一個「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的版本。在這樣的觀點中,自己內心的聲音就被視為是自己思考的過程。自然語言在這樣的觀點中,比較像是額外的心理表徵。嬰兒會有思考的語言;而成人在思考的語言之外,額外有一個自然語言(可能是英語、華語會任何語言)。
是文化影響認知?還是語言影響認知?
Lucy and Gaskins (2001)有一系列的研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先讓受試者看目標物,接著會給受試者兩個選項,讓他們選擇其認為和目標物最相似的物品。一個物品和目標物的形狀是一樣,但是材質是不一樣的;另一個物品則是相同材質,但是形狀不一樣。受試者不會聽到任何新的詞語。英語母語者的選擇傾向以形狀來決定兩個物品的相似;但是來自墨西哥的一個馬雅語言尤卡特語(Yucatec Maya)人則傾向根據材質。
為什麼語言可以被視為是有結構的想法?語言決定論的邏輯。
Bloom (2000) 提供了我們一些語言決定論的想法:
請想像一個水平線,最左邊三分之一的部分我們叫它「zoop」,剩下的部分則是「moop」。一開始,我們對這條水平線沒有任何想法,但是經過上面的過程後我們對這條水平線有了結構。這就是認知的結果。例如:你可以知道這條線被平均地分為三等分,然後可以概據這樣子的線索,知道兩個zoop就和一個moop是一樣的。
請想像一個水平線,最左邊三分之一的部分我們叫它「zoop」,剩下的部分則是「moop」。一開始,我們對這條水平線沒有任何想法,但是經過上面的過程後我們對這條水平線有了結構。這就是認知的結果。例如:你可以知道這條線被平均地分為三等分,然後可以概據這樣子的線索,知道兩個zoop就和一個moop是一樣的。
小孩子是先有思想才有語言?還是先有語言才有思想?
有許多人認為小孩子在學習語言之前,就已經知道一些東西了,小孩子只是不知道名稱而已。Fodor (1975)認為這樣子的觀點把所有語言學習都當成是二語學習了。在還沒接觸詞語(例如:華語)之前,小孩子已經可以和詞語對應的概念,它是將簡單的概念以有系統的方式組織起來,是謂「思考的語言假說」(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或者心理語(mentalese)。
閱讀理解和詞彙能力有什麼關係?
增加閱讀理解,就能夠幫助詞彙的增加(Beck,Perfetti & McKeown, 1982; Kameenui,Carnine & Freschi, 1982; Stahl, 1983),這樣子的說法經Davis (1944) 分析了許多因素之間的關係後,也發現這閱讀理解和詞彙增加確實存在互相彼此影響的關係。
學習第二語言詞彙和學習第一語言有何異同?
對於剛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詞彙學習,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他們能夠聽、說、讀、寫的詞彙是幾乎一致的;二、初期的詞彙都只是將學習者既有的概念和一個新的標籤連結在一塊而已。
這樣子的特徵和學習第一語言詞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在第一語言的時候,聽、說、讀、寫的詞彙是有很大的差異的(Deighton, 1960);而且,學習一個新的標籤時,也同時學得一個新的概念(Mezynski, 1983)。
一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進步飛快,但是當學習者要從初階閱讀到進階閱讀的時候,學習的困難就會發生了。剛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學生所閱讀的是經過簡化的文本,但是當學生開始接觸未經簡化的真實文本時,接觸的單字不再由教科書所控制。也由於學習者所閱讀的文本通常是缺乏背景知識的文本,例如標的語人們的文化或風俗,於是學習者會開始認為學習第二語言不再如同一開始那樣容易。
一但過了上面的階段,學習第二語言詞彙的方式就會更接近第一語言的方式。學習者不再只是學一個已知概念的標籤,同時要學會新的概念。
這樣子的特徵和學習第一語言詞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在第一語言的時候,聽、說、讀、寫的詞彙是有很大的差異的(Deighton, 1960);而且,學習一個新的標籤時,也同時學得一個新的概念(Mezynski, 1983)。
一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進步飛快,但是當學習者要從初階閱讀到進階閱讀的時候,學習的困難就會發生了。剛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學生所閱讀的是經過簡化的文本,但是當學生開始接觸未經簡化的真實文本時,接觸的單字不再由教科書所控制。也由於學習者所閱讀的文本通常是缺乏背景知識的文本,例如標的語人們的文化或風俗,於是學習者會開始認為學習第二語言不再如同一開始那樣容易。
一但過了上面的階段,學習第二語言詞彙的方式就會更接近第一語言的方式。學習者不再只是學一個已知概念的標籤,同時要學會新的概念。
References
Anders,
P. L. & Bos, C. S. (1986). 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 An
Interactive Strategy for Vocabulary Development and Text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ading, 29(7), 610-616.
Beck,
I. L. & McKeown, M. G. (1985). Teaching vocabulary: Making the
instruction fit the goal.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23(1),
11-15.
Beck,
I. L., Perfetti, C. A. & McKeown, M. G. (1982). Effects of
long-term vocabulary instruction on lexical acces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4(4), 506.
Carr,
E. & Wixson, K. K. (1986). Guidelines for Evaluating Vocabulary
Instruction. Journal of Reading, 29(7), 588-595.
Davis,
F. B. (1944). Fundamental factors of comprehension in reading.
Psychometrika, 9(3), 185-197.
Deighton,
L. C. (1960). Developing vocabulary: Another look at the problem. The
English Journal, 49(2), 82-88.
Dunmore,
D. (1989). Using Contextual Clues to Infer Word Meaning: an
Evaluation of Current Exercise Types Don Dunmore.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6(1), 337.
Hague,
S. A. (1987). Vocabulary instruction: What L2 can learn from L1.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3), 217-225.
Harvey,
P. (1983). Vocabulary learning: the use of grids. ELT journal,
37(3), 243-246.
Kameenui,
E. J., Carnine, D. W. & Freschi, R. (1982). Effects of text
construction and instructional procedures for teaching word meanings
on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
367-388.
Kameenui,
E. J., Dixon, D. & Carnine, D. W. (1987). Issues in the design of
vocabulary instruction. In (), The nature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Meara,
P. (1980).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 neglected aspect of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13(3-4), 221-246.
Mezynski,
K. (1983). Issues concerning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Effects of
vocabulary training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3(2), 253-279.
Morgan,
J. & Rinvolucri, M. (2004). Vocabul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gy,
W. E. & Herman, P. A. (1985). Incidental vs.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to Increasing Reading Vocabulary.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23(1), 16-21.
Nelson-Herber,
J. (1986). Expanding and Refining Vocabulary in Content Areas.
Journal of Reading, 29(7), 626-633.
Stahl,
S. (1983). Differential word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ading Behavior, 15(4), 33-50.
Stoller,
F. & Grabe, W. (1993). Implications for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instruction from L1 vocabulary research. In (),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Ablex.
Thelen,
J. N. (1986). Vocabulary Instruction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Journal
of Reading, 29(7), 603-609.
CLIL具體怎麼進行?一個用英語上體育課的例子。
Heras and Lasagabaster (2015)有這樣子的例子。西班牙有17個行政區,有6個是雙語區。娜瓦利(Navarre)是巴斯克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區。在一個鄉下地方的國民中學就有機會參加不同計畫的CLIL課程。以一個不具名的國民中學為例,它可能會參加以法語學習歷史和地理的CLIL課程,同時參加以英語學習體育的CLIL課程。
動機和第二語言習得在不同時期的文獻告訴我們什麼?
Dörnyei and Ushioda (2009)回顧文獻,將第二語言習得在動機的文獻上分為三個階段:社會心理期(1959-90)、認知環境期(1990s)和社會動態期(21世紀的轉向)。
在社會心理期,研究主要來自加拿大。加拿大因為語言的關係,使人們分為英語圈和法語圈的分化,因此這時候的研究旨在了解對於學習另外一個族群語言的動機是不是能夠消彌不同社群的歧見。當學習者比較正面地看得另一個社群,且有想和另一個社群溝通的慾望,那就有較好的學習。這是有一點兒融合的意味(integrative orientation或integrativeness)。
在社會心理期,研究主要來自加拿大。加拿大因為語言的關係,使人們分為英語圈和法語圈的分化,因此這時候的研究旨在了解對於學習另外一個族群語言的動機是不是能夠消彌不同社群的歧見。當學習者比較正面地看得另一個社群,且有想和另一個社群溝通的慾望,那就有較好的學習。這是有一點兒融合的意味(integrative orientation或integrativeness)。
研究動機和第二語言習得,可以用什麼框架進行?
動機在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中,一直有許多討論。有很長一段時間,文獻認為動機是一個穩定且線性的關係;但是,近二十年來,也開始有比較動態的觀點。主要是因為,這些關於動機和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都是在不一樣的脈絡下進行,這使得動機對於語言學習有不一樣的關係(Masgoret & Gardner, 2003) 。另外,之所以有許多學習者對於第二語言學習的動機減弱,除了教學方法之外,學習者的心理變化,例如拒絕整個學校系統也可能是原因。CLIL有沒有辦法使動機改變呢?
學詞彙是不是有最好的策略?
Sanaoui (1995)的質化研究中觀察在英屬哥倫比亞學習法語作為二語的學習者,其認為學習者的語言程度和教學方式並不會影響詞彙的學習,真正影響個人詞彙學習是其是否有結構(structured/ unstructured)。
二語學習者能否像母語者一樣,從脈絡猜出詞語的意思?
對於母語者而言,脈絡中有一個不認識的詞語而其它都是認識的詞語是常見的狀況;而二語學習者則可能是在一個段落裡頭就有無數的個不認識的詞語。當段落中有多個不認識的詞語時,就很容易迷路或誤導 (Folse, 2002; Folse & Briggs, 2007)。即是母語者在脈絡下去猜測新詞的詞義,也不見得能夠受益於脈絡(Schatz & Baldwin, 1986)。(Folse, 2004)認為要求二語學習者去從脈絡中猜出新詞的詞義是沒有道理的。
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使用翻譯真的不好嗎?
有許多的實證研究都證明第一語言的翻譯在第二語言學習有其價值。
Hulstijn,Hollander and Greidanus (1996)比較閱讀文章旁邊用學生的一語和二語的注釋(marginal gloss),結果發現以學生的一語比較容易幫助學習,Laufer and Shmueli (1997)也呼應這樣的結果;Lotto and De Groot (1998) 則比較以第一語言和圖片作為示意的情況,結果發現以學生的一語比圖片的呈現,學生對於新詞記得更久(retention);Grace (1998)則發現英語母語者學法語的時候,學習者認為在能夠有一語的情況下,比較容易確認正確的意思;Prince (1996)發現,透過一語翻譯的情況對於程度較差的學習者而言,比較容易能夠去回想(recall)起新詞。
這並不是說學習二語一定要依靠第一語言翻譯,第一語言之所以有價值,在於其能夠讓學習者將新知識和舊知識連結在一起,去激發已經穩固的詞彙網絡。學習新詞的時候,之所以要激發先前的知識的因為它以經是個連結綿密的資訊網,一但新的詞彙能夠整合到這個資訊網裡頭,只要有一點點連結,學習者就容易喚回詞彙。許多研究都支持這樣子的說法(Stahl, 1983; Stoller & Grabe, 1993; Martin,Martin & Ying, 2002; Schmitt and Schmitt (1995) 。
Hulstijn,Hollander and Greidanus (1996)比較閱讀文章旁邊用學生的一語和二語的注釋(marginal gloss),結果發現以學生的一語比較容易幫助學習,Laufer and Shmueli (1997)也呼應這樣的結果;Lotto and De Groot (1998) 則比較以第一語言和圖片作為示意的情況,結果發現以學生的一語比圖片的呈現,學生對於新詞記得更久(retention);Grace (1998)則發現英語母語者學法語的時候,學習者認為在能夠有一語的情況下,比較容易確認正確的意思;Prince (1996)發現,透過一語翻譯的情況對於程度較差的學習者而言,比較容易能夠去回想(recall)起新詞。
這並不是說學習二語一定要依靠第一語言翻譯,第一語言之所以有價值,在於其能夠讓學習者將新知識和舊知識連結在一起,去激發已經穩固的詞彙網絡。學習新詞的時候,之所以要激發先前的知識的因為它以經是個連結綿密的資訊網,一但新的詞彙能夠整合到這個資訊網裡頭,只要有一點點連結,學習者就容易喚回詞彙。許多研究都支持這樣子的說法(Stahl, 1983; Stoller & Grabe, 1993; Martin,Martin & Ying, 2002; Schmitt and Schmitt (1995) 。
References
Grace,
C. A. (1998). Retention of Word Meanings Inferred from Context and
Sentence-Level Trans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Beginning-Level CALL Softwar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4),
533-544.
Hulstijn,
J. H., Hollander, M. & Greidanus, T. (1996).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by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The
influence of marginal glosses, dictionary use, and reoccurrence of
unknown word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3), 327-339.
Laufer,
B. & Shmueli, K. (1997). Memorizing new words: Does teaching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RELC journal, 28(1), 89-108.
Lotto,
L. & De Groot, A. (1998). Effects of learning method and word
type on acquiring vocabulary in an unfamiliar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48(1), 31-69.
Martin,
M. A., Martin, S. H. & Ying, W. (2002). The Vocabulary
Self-Collection Strategy in the ESL Classroom. TESOL Journal,
11(2), 34-35.
Olsen,
S. (1999). Errors and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A study of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n texts written by Norwegian learners of English. System,
27(2), 191-205.
Prince,
P. (1996).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The role of context
versus translations as a function of proficienc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4), 478-493.
Schmitt,
N. & Schmitt, D. (1995). Vocabulary notebook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ELT journal, 49(2),
133-143.
Stahl,
S. (1983). Differential word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ading Behavior, 15(4), 33-50.
Stoller,
F. & Grabe, W. (1993). Implications for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instruction from L1 vocabulary research. In (),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Ablex.
Tinkham,
T. (1993). The effect of semantic clustering on the learning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System, 21(3), 371-380.
Tinkham,
T. (1997). The effects of semantic and thematic clustering on the
learning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3(2), 138-163.
Waring,
R. (1997).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earning words in semantic sets: A
replication. System, 25(2), 261-274.
呈現新詞的時候,應該以語義組合還是主題組合?
大多數的課程或教材在呈現詞彙的時候,會以語義組合呈現,例如:家庭成員、動物或星期,比較少課程會以一個主題來包含新詞。關於以主題組合的例子可以見這個網頁。
語言教師呈現詞彙的時候,以語義組合或主題組合來呈現比較好呢?Tinkham (1993)發現,當學習者以語義組合來學習新詞的時候會比較困難。Waring (1997)則發現日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二語時,學習相關的詞彙組合,比起學習完全不相關的詞彙組合,前者比後者需要多花一半的時間。而Tinkham (1997)則發現語義組合對於學習有負面影響,而主題組合能夠促進學習。Olsen (1999)則發現挪威的英語二語學習者容易被語音相似而混淆,例如sea和see或want和won’t。
語言教師呈現詞彙的時候,以語義組合或主題組合來呈現比較好呢?Tinkham (1993)發現,當學習者以語義組合來學習新詞的時候會比較困難。Waring (1997)則發現日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二語時,學習相關的詞彙組合,比起學習完全不相關的詞彙組合,前者比後者需要多花一半的時間。而Tinkham (1997)則發現語義組合對於學習有負面影響,而主題組合能夠促進學習。Olsen (1999)則發現挪威的英語二語學習者容易被語音相似而混淆,例如sea和see或want和won’t。
References
Grace,
C. A. (1998). Retention of Word Meanings Inferred from Context and
Sentence-Level Trans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Beginning-Level CALL Softwar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4),
533-544.
Hulstijn,
J. H., Hollander, M. & Greidanus, T. (1996).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by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The
influence of marginal glosses, dictionary use, and reoccurrence of
unknown word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3), 327-339.
Laufer,
B. & Shmueli, K. (1997). Memorizing new words: Does teaching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RELC journal, 28(1), 89-108.
Lotto,
L. & De Groot, A. (1998). Effects of learning method and word
type on acquiring vocabulary in an unfamiliar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48(1), 31-69.
Martin,
M. A., Martin, S. H. & Ying, W. (2002). The Vocabulary
Self-Collection Strategy in the ESL Classroom. TESOL Journal,
11(2), 34-35.
Olsen,
S. (1999). Errors and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A study of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n texts written by Norwegian learners of English. System,
27(2), 191-205.
Prince,
P. (1996).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The role of context
versus translations as a function of proficienc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4), 478-493.
Schmitt,
N. & Schmitt, D. (1995). Vocabulary notebook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ELT journal, 49(2),
133-143.
Stahl,
S. (1983). Differential word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ading Behavior, 15(4), 33-50.
Stoller,
F. & Grabe, W. (1993). Implications for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d instruction from L1 vocabulary research. In (),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Ablex.
Tinkham,
T. (1993). The effect of semantic clustering on the learning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System, 21(3), 371-380.
Tinkham,
T. (1997). The effects of semantic and thematic clustering on the
learning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3(2), 138-163.
Waring,
R. (1997).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earning words in semantic sets: A
replication. System, 25(2), 261-274.
參加詞彙課程的學生對於詞彙學習方法的態度有什麼樣的改變?
大多數語言研究者和教師對於詞彙的關注較少,因為在封閉的系統下,例如:句法和語音,人們是比較容易進行歸納和演繹(Richards, 1976; Laufer, 1986)。但是,比較大學二語學習者的偏誤比例時,卻發現詞彙的偏誤高於語法的3倍到4倍(Meara, 1984)。學習者的詞彙能力和其學術成就有很大相關,特別影響閱讀的表現(Laufer, 1986; Qian, 2002)。Paribakht and Wesche (1996)指出,在以理解為基礎的上所進行的課程,即能夠對學習者的詞彙能力有大大的提升。
詞彙教學怎麼做?
Schmitt (2008) 認為刻意為之的詞彙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有三個原則:一、透過活動使學習者對於目標詞彙的參與程度最大化;二、透過重覆的出現使學習者對於目標詞彙的接觸最大化;三、考量詞彙不同面向的知識。
為什麼需要詞彙教學?
目前,大眾所偏好的語言教學型式是以意義為基礎的學習(meaning-based learning),在這樣的型式下,學習者是學習「使用語言特徵」(using language features),而不是學習「語言特徵」(language features),只有在需要的時候以輔助的方式給予補充。這樣子的語言教學型式為學習者建立聽、說、讀、寫四個基本能力以及語法結構或許有所助益,但是對於詞彙的學習,可能需要有不一樣的取徑才能讓學習者將注意力轉移到詞彙本身。
一個詞彙從零到精熟是怎麼樣的過程?
Henriksen (1999) 認為詞彙的知識是從零開始,然後有部分的知識,最終到精熟。這意味著,學習詞彙並不是非有即無,而是一個連結的過程。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說一個詞彙是如何經歷這樣的過程。Schmitt (2010) 認為一個詞彙的發展可能是這樣:初始階段(剛開始的幾次接觸),可能對於形式、意義和詞性有點認識;接著,形式、意義和詞性幾乎達到精熟後,詞語脈絡的知識(contextual word knowledge)也開始發展,但是仍不太熟練;最後,詞語脈絡的知識也都趨於完備,但是仍不到精熟,畢竟母語者也無法宣稱能夠精熟任何詞語的脈絡知識。
老師上課教過詞語後,學習者還需要做什麼嗎?
課程中,老師透過循環讓詞語的學習更好;課程後,學習者必須透過複習再鞏固(consolidating)詞彙。從(Schmitt, 2000; 131) 的遺忘軌跡來看,在課程學習後馬上複習是最好的時間,然後隨著時間前進會隨著遺忘而留下的記憶會越來越少。 (Russell, 1979; 149) 建議在學習後的五到十分鐘、二十四小時、一個星期、一個月和六個月後進行複習,是一個可用來作為鞏固記憶、按表操課的時間。如此,遺忘的可能性會大幅地減低。
學習者應該要接觸幾次新詞,才能學習會一個詞?
從過往的研究來看,研究者們認為能夠學會一個詞所需要的接觸次數在5次到16次之間(Nation, 1990) (Nation1990)。之所以存在5次到16次這麼大範圍的變異,Schmitt (2010) 認為和接觸時的方式以及學習者投入的程度有關。
我們如何理解雙語者的心理詞典?
人們的心理詞典(mental lexicon)是如何組織、如何運作的呢?我們馬上可以想出兩個可能的解釋因素:一、頻率。當我們進行詞彙聯想的時候,會從腦海裡跳出來的詞彙通常就會是我們常常遇到的詞彙。語料庫是最容易計算詞彙頻率的,但是語料庫卻無法預測人們詞彙聯想的結果。畢竟,詞彙聯想是相當個人的行為,不論對母語者或二語者來說都是如此。二、語言程度。如果說語言程度不會影響心理詞典那也很奇怪,程度低的可能連刺激詞彙都不認得,和程度好的相比,聯想的結果肯定會有差別。但是,我們在判斷二語者的語言程度時,是以一個典型的母語者的程度作為標準。當單一母語者產生的聯想詞彙是有別於一般母語者的話而如同二語者的話,那豈不是母語者的語言程度如同二語者了?過去也有研究指出,語言程度並不能作為解釋人們對於自由聯想產生變項的原因(例如:Den Dulk (1985) 和Kruse,Pankhurst and Smith (1987) 的研究)。
詞語自由聯想測驗在母語者和二語學習者身上有什麼樣的異同 ?
對於受試者因應詞語聯想(word association)測驗的反應,研究者將它們分成三種類別:聚合類(paradigmatic)、組合類(syntagmatic)以及和詞語意義本身較沒有關係的類別(phonological, clang)。反應被歸在聚合類通常和刺激詞彙屬於同一個詞類,在給定的句子下,有相同的句法功能。聚合類的反應大概可以再分成四類:同級別(coordinates)、上屬級(superordinates)、下屬級(subordinates)以及同義級(synonyms)。以「狗」為刺激詞語為例,反應為「貓」,則是同級別;反應為「動物」,則是上屬級;反應為「柴犬」,則是下屬級;反應為「犬」,則是同義級。組合類則會是和刺激詞語常常共同出現的關係,同樣以「狗」為例,反應若為「吠」或「咬」,這樣的詞語,則是組合類。而因為聲音而聯想出來的反應,刺激詞語為「狗」,而反應出來的為「夠」那就會被視為是第三類。
由母語者參加詞語聯想測驗,比較不同年紀學童的反應類別數量,發現學童的年紀越大,產生聚合類別的反應比例越高,而第三類的反應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減少(Brown & Berko, 1960; Ervin, 1961; Entwisle, 1966; Palermo, 1971)。從組合類轉變成聚合類(syntagmatic-paradigmatic shift)被認為是詞彙或認知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這樣的轉變被認為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也會發生在每個詞語上(Wolter, 2001)。
由母語者參加詞語聯想測驗,比較不同年紀學童的反應類別數量,發現學童的年紀越大,產生聚合類別的反應比例越高,而第三類的反應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減少(Brown & Berko, 1960; Ervin, 1961; Entwisle, 1966; Palermo, 1971)。從組合類轉變成聚合類(syntagmatic-paradigmatic shift)被認為是詞彙或認知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這樣的轉變被認為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也會發生在每個詞語上(Wolter, 2001)。
我們如何描述二語學習者的詞語知識?
如何知道一個人的詞語知識規模(Vocabulary Knowledge Scale),Nagy,Herman and Anderson (1985) 透過訪談的方式,Wesche and Paribakht (1996) 將訪談的方式改為紙筆測驗,如此可以大規模施測。在給定目標詞語言,學習者回答:
不同的詞語知識測驗間,是否可以互相參照?
雖然都是測量詞語的知識,但是不同測驗間還是會些許的差別,Paul,Stallman and Rourke (1990) 比較二語學習者的選擇題、面試以及自評是否知道這個詞(Yes/No)三種測驗,發現三者的相關係數介於.66到.81之間。但是Nist and Olejnik (1995) 的研究,對於母語者在同樣的詞彙下進行造句、完成句子、意義與範例的四種測驗,則發現彼此的相關通通低於.7。Laufer and Goldstein (2004) 也在他們研究中的四種測驗發現測驗間的相關不高。
測量二語學習者的詞語知識時,我們是想知道什麼?
測量人們的詞語知識時,我們會關心兩個事情:一、某個特定的字是否為學習者所熟悉;二、對於詞語背後系統性的規律是否有意識(Nation, 2013) 。舉例來說,要求學習者去拼出agree、balloon和practice的時候,我們可能關心學習者是否能拼出這三個詞語;但是我們也可能測試學習者swimming、occurrence或spinner,這時候可能想知道的是學習者是否知道兩個子音可以接連出現的規律。若要知道隱藏在詞語背後的規律,則必須對於材料有很好的控制。對於詞語背後的規律的測驗是非常缺乏的。
CLIL下的教材和活動任務如何評估?
理想中的CLIL學程可以從教材設計或活動任務設計中看出端倪,因此教材和活動任務也是很重要的證據之一。一個好的CLIL學程對於是由老師引導(teacher-directed)或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red)並沒有任何一定要遵循的要求。提供鷹架式地支持(scaffolding)是CLIL很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學習者的語言尚末全面發展前。
CLIL下的學習過程如何評估?
「學習」如何在CLIL的學程下發生?我們需要從學習過程(process)的證據來評估。在課堂中,小組活動時的會話如果能夠轉寫成逐字稿,這對於不了解CLIL的人來說,就有一個認識CLIL的視窗。或者,利用Coyle,Hood and Marsh (2010b) 建議的LOCIT(Lesson Observation and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的方式,將課堂上學習發生的時刻剪輯成不到15分鐘的影片,和學生、和同儕一起分析、探討,也是可以評估學程能夠對於學習過程產生的影響。
CLIL對於學習者和老師的動機有什麼影響?
有較高的動機,就可以使學習者有更深入、專注的學習,當然,最重要的是確保其在目標語言的學習感就。因此,提供情感方面的證據,也是CLIL讓自己可以被社會接收的方式。透過大規模的問卷或焦點團體訪談都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據。
CLIL產生對於語言學習有什麼樣的影響?它只適合程度較好的學生嗎?
大多數評估CLIL學程中,學習者的表現仍多集中在語言的表現。Lasagabaster (2008) 比較了雙語者(在CLIL下學習)和非雙語者(在非CLIL下學習)在標準化測驗下(Cambridge ESOL)下的表現。雙語者本來就有天份和動機,在語言表現(接收技能和產出技能)上比較好是不證自明,但是Lasagabaster (2008) 的研究發現,在非CLIL下的學習者,其學習表現會因為性別和社經地位產生差異;但在CLIL下的學習者,則沒有這樣子的差異。這似乎說明,CLIL是可以跨越性別和社經地位,一體適用的教育取徑。 Ruiz de Zarobe (2008) 比較產出的種類和數量的比例(type/tokens ratio)也是CLIL組的表現較好。
我們可以從哪些證據來評估CLIL的影響?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是一平衡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的教育取徑,透過標的語作為媒介,使內容和語言可以同時被學習。馬來西亞的教育中,使用英語學習數學和科學就是這樣子取徑的例子。如果這樣子的教育取徑不是作為眾多語言教學方法之一,而是被持續、長久地運用在某個學程下,這對於學習者、教師、教材或活動任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將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LIL)實踐於華語短期班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是一平衡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的教育取徑,透過標的語作為媒介,使內容和語言可以同時被學習。馬來西亞的教育中,使用英語學習數學和科學就是這樣子取徑的例子。
我們說學會一個詞,是能夠聽/看得懂一個詞?或者還包括會說/寫一個詞?這兩者有什麼關係?(Nation, 2013)
當我們說一個二語學習者「學會一個詞語」時,它可能指的是很多可能。這取決於我們認為「詞語知識」的構念為何!一個簡單地分類是依據語言傳遞的方向分為可以接受、理解的被動性詞彙(passive vocabulary)知識,以及能夠產出「主動性詞彙」(active vocabulary)。Laufer (1998)比較三種詞彙知識:被動性詞彙(passive)、控制下的主動性詞彙(controlled active)以及自由的主動性詞彙(free active),三種知識分別以不同的測驗形式進行。在16歲大的學習者身上發現,被動性詞彙都是會多於主動性詞彙,而且隨著年紀越大,被動性和主動性詞彙的差距會越來越大。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將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華語教學上?
1980年代末期,測量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口語和書面的產出)有了三個方面:複雜度、準確度以及流暢度(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CAF)(Skehan, 2009)。複雜度指的是從屬子句的數量,如果計算T- Unit(minimum terminable unit,最小可斷單位)的話,數量越多,則複雜度越高。準確度則指的是正確使用語言、沒有錯誤的比例。流暢度則是在實際使用語言的時候,不會有任何不必要的猶豫、停頓,它同樣可以由T- Unit或子句的長度來呈現(Skehan, 2009)。這個雖然說是第二語言語言表現的測量,但對於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來說,可能不能完全套用。
泰國怎麼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是持續進步?系所評鑑可能是方法
今年(2017年),教育部宣布未來大學的系所評鑑,往停辦的方向規劃,讓系所評鑑從「依法辦理」到「依需要辦理」,系所評鑑可能不再由教育部發起,而是由大學自主決定是不是進行。對於我這樣的無名小卒,是很少有機會能夠體會系所評鑑的,頂多也就是在系所要參加評鑑的時候,擔任臨時工讀生,幫忙整理文件。大概可以片面從老師們、助教們的口中體會到,這是需要很多紙上功夫的工作。當系所評鑑變成文件的準備,那就很容易流於形式。我有幸在泰國擔任華語老師的時候,參與了一次泰國的系所評鑑,我才知道系所評鑑對於大學而言是多麼重要的過程。
學習第二語言詞彙的時候,詞語表是否真的毫無用處?(Folse, 2004)
Laufer and Shmueli (1997)比較四種呈現詞語的方式:一、只有詞語;二、詞語加上簡短的脈絡;三、把詞語放在句子脈絡;四、把詞語放在文章裡頭。猶太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為外語的學生在這四種方式下學習詞語,測驗其學習後能夠記得多少語詞,結果發現前兩種的得分高於後兩種。
訂閱:
文章 (Atom)